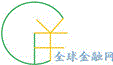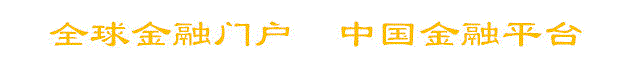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 No.2017/2
PBC Working Paper No.2017/2
2017年3月20日
March 20,2017
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国际前沿
徐忠1
摘要: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责以来,在经济约束和结构性特征异常复杂的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当局根据中国经济金融的实际和宏观调控的需要,不断突破思想束缚,积极探索和初步形成了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体系和理论基础。全球金融危机对传统货币经济学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这极大推动了理论界和决策者的深刻反思。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实践和宝贵经验,同时全面梳理了危机以来国外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货币政策框架的新方向、货币政策操作的新模式和货币政策调控策略的新变化。事实证明,中国金融宏观调控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的反思是一致的,有必要加以总结完善。这对于做好新常态下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Abstract: As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world’s biggest emerging,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al economy, considering the extreme complicated constraints and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mainstream theory are focusing on developed economies, PBC actively explore monetary policies not only based on international theory progresses and experiences but also on the Chinese conditions status quo, successfully promote growth and price stability, and achieve satisfactory policy outcomes.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monetary economics,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reflection and progres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theory. In this article, we mad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rontier progress and new models of the monetary economics theory,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operations as well as strategies, and analyzed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practice, which are the same in essence. Therefore, we can draw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both in theory and policy to transform the monetary policy, perform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under nowadays China’s new normal.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货币理论;货币政策;中国经验
声明: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发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如需引用,请注明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
Disclaimer: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C) publishes research reports written by staff members of the PBC,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cholarly exchanges. The views of these reports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PBC. For any quotations from these reports, please state that the source is PBC working paper series.
1徐忠,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本文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
2
一、引言
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各国中央银行政策实践为做好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但是,主流经济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作为现实背景,理论的进展也主要是为了解决发达国家出现的新问题。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由世界经济边缘到全球举足轻重的巨大变迁中,国外主流经济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宏观调控并不完全具有直接的针对性。如果简单地按照既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政策,很有可能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迫切需要,促使中国货币政策当局不仅要突破固有计划经济禁锢,更要清醒避免唯洋是举、食洋不化,积极突破思想束缚,努力开展政策探索,通过不断解决经济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传导存在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在顺利实现产出和物价稳定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同时,确保经济金融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责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探索,逐步实现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第一次重大转型,即从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以间接调控为主,并逐渐形成了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以维持物价稳定为最终目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运用的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与此同时,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就改革经验而言:一是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强调突出价格稳定并兼顾其他目标;二是按照间接调控要求改革完善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三是根据发展阶段和国情需要,选择实施数量、价格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调控模式;四是始终注意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金融改革相互结合,重视“在线修复”金融体系,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实践,这一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日臻成熟,不仅经历了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而且在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的各个经济周期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调控效果。
在成功走出“滞胀”泥潭后,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发达国家进入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较高增长和稳定通胀的“大缓和”时代,货币经济理论的进展对此功不可没。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以存在市场摩擦和粘性价格等更接近现实的结构特征作为微观基础并进行长期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NNS)获得了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广泛认可。以通货膨胀作为最主要目标并(隐含地)在一定规则(泰勒规则,Taylors Rule, Taylor, 1993)下仅调整短端(主要是隔夜)利率工具成为各主要中央银行普遍采用的货币调控模式。但是,货币经济学理论总是与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而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百年一遇金融海啸”冲击下,原本“成熟”的货币经济学理论暴露出明显的范式缺陷,以此为指导并成功管理经济的货币政策当局不得不进行大量史无前例的创新性政策实验,这极大推动了理论界的深刻反
3
思。目前,国际学术界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和货币政策调控策略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理论和政策实践来看,各国情况存在差异,但也有不少有共性的问题。
事实证明,中国金融宏观调控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的反思是一致的,有必要加以总结完善。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货币政策面临的约束更加复杂。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跟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币经济分析理论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最新进展,充分发挥中国货币政策的成功经验和体制优势,对于做好新常态下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宏观经济学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趋向
自Keynes(1936)开创宏观经济学以来,宏观经济理论就被应用于政策实践,而宏观经济和货币调控面临的现实问题,又使得货币当局不得不尝试政策创新,从而促使人们对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深刻反思。宏观经济理论与货币政策就是在一次次危机的实践检验中不断探索,日臻成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理论思想上再次表现出明显的凯恩斯主义特征,而从模型方法来看,如何更好地将金融因素引入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对模型结构进行更准确地刻画、更准确估计模型参数并结合传统计量模型进行经济分析,成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凯恩斯主义回归
通过引入价格粘性并考虑总供给和总需求(IS-LM)的一般均衡方法,Keynes(1936)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Neo Classical)市场完美假设,提出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各国政策干预经济以熨平经济波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二战”后宏观经济学主流。但是,传统凯恩斯主义往往仅关注宏观总量关系,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没有考虑微观主体行为及政策对微观决策和激励机制的影响,而且主要侧重于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往往采用静态或适应性预期处理长期动态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Lucas, 1976)问题,以传统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存在严重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各国最终陷入痛苦的滞胀困境。在以Friedman(1968)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和以Lucas(1976)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大力推动下,主张经济自由的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淡化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粘性和需求波动,转而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成为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
Friedman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倡导者,他推动的货币主义理论主要采用局部均衡比较静态方法并通过适应性预期方式处理经济动态问题(Smithin, 2003)。不过,1970年代以来各国货币数量目标制的实践效果不佳,货币主义逐渐淡出。货币经济分析应采取具有微观基础、理性预期和一般均衡特征的结构化方法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DeJong and Dave, 2007; 刘斌,2016)。在完全市场条件下,
4
Kydland and Prescott(1982)开创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建立在微观经济人理性预期之上,能够有效克服卢卡斯批判,并对于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理论解释,因此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们的推崇。不过,在完全市场假设下,RBC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源自技术冲击而与金融无关,而且RBC模型由于没有价格粘性假设,因此并不包含货币政策。事实上,在完全竞争和价格充分弹性下,Cooley and Hansen(1989)利用RBC方法的分析表明,货币只能影响物价等名义变量,并不对产出等实体变量产生影响,这也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无法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帮助。不仅如此,RBC理论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供给侧所驱动而与需求无关。如果价格能够足够灵活调整,那么经济产出波动就是供给波动的最优反应,货币当局任何试图烫平经济波动的努力都是多余。RBC模型目前并不为货币当局所广泛认可。尽管其它新古典宏观模型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得到货币短期非中性效果(Lucas, 1972),近年来也有在完全市场假设下,通过考虑银行部门作用在DSGE框架下进行货币政策分析(Basu et al.,2012),但由于理论和政策分析的局限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对政策制定产生广泛影响。
由于以RBC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理论有效市场假设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因而对经济的解释往往并不理想。同时,通过菜单成本、交错定价等方式,很多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 NK)经济学家发展出大量具有微观基础的价格粘性模型(Mankiw, 2006)。1990年代以来,借鉴RBC方法,引入具有微观基础的不完全竞争价格粘性NK模型更符合现实,对经济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可以有效开展政策评估,因此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各国中央银行的青睐。目前在各国中央银行广泛使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都是原始NK模型结合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拓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NK的价格粘性特征与传统凯恩斯主义相同,但理性预期条件下的建模方法与新古典宏观是一致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 Samuelson, 1955),这也是其又被称作新新古典综合(Goodfriend and King, 1997)的原因。NK模型更接近经济现实,既包含了传统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涵,又强调了预期管理对于实现最优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因而成为现代货币经济分析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政策研究主流的方法。以NK模型为参考的货币政策通过在“大缓和”时期的成功表现,极大增强了经济学家们通过政策的精准调整实现产出和物价稳定的信心。
全球金融危机后,基于“大萧条”的教训,各国都通过大规模刺激性政策成功避免了危机的迅速蔓延,这正是凯恩斯主义典型的反周期需求管理操作。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初期经济恶化状况是超过大萧条的,由于及时和猛烈的扩张性需求管理,危机只是导致大衰退而没有发展成为大萧条(Furman,2014)。同时,各国都意识到财政政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经济持续低迷并很可能进入长期性停滞的当下,如何将金融稳定、宏观政策协调、贫富差距、各国政策协调等结构性问题融入NK模型,成为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
(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
1、将金融因素系统引入DSGE模型框架
5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宏观模型对危机冲击的深度和衰退持续时间普遍估计不足,出现过于乐观的系统性偏差,这主要与其未能将金融系统纳入模型分析中有关。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很少讨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实体经济的影响。19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从理论上认识到信息不对称对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性(Stiglitz and Weiss,1981)。很多关于经济危机(包括“大萧条”)的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摩擦将引发经济运行不稳定(Mishkin, 1997)。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使宏观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充分认识到,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与经济的关系比之前想象得更为重要,再也不能忽视金融系统对于宏观经济的作用了。
事实上,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学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传统宏观模型没有金融机构的缺陷。这一缺陷导致在传统模型里信贷的波动只能由需求方也就是企业的需求波动来引发,而这与在大萧条和日本经济危机中观察到的金融机构本身供给信贷能力受损导致信贷剧烈波动从而放大危机的现象明显不符。为此,经济学家们试图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Bernanke and Gertler, 1986)、抵押品约束机制(Kiyotaki and Moore,1997)和考虑特定形式金融部门的生产函数(Goodfriend and McCallum,2007)等三种方式将金融因素引入传统宏观模型。从建模思路来看,上述三种方法的核心都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分析由于金融系统摩擦导致信贷供给(而非信贷需求)变化对经济波动的放大作用,而且建模方法上还有所交叉,但危机前的主流宏观模型都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次贷危机出乎意料的原因之一。
2、对经济结构进行更准确地刻画
需要认识到,DSGE模型属于结构化分析方法,基于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分析,很容易出现模型设定错误从而导致分析出现较大偏差。因而,对经济结构更准确的刻画是DSGE模型方法和宏观经济分析发展的主要方向,除了系统引入金融因素外,还包括利用投入产出信息引入多个部门,重新审视经济趋势与波动的关系,考虑非基本面的消息冲击,引入异质性微观主体、扩展开放条件和调整通胀动态机制等方面(Yellen, 2016c)。
(三)以符合中国实际的坚实理论为支撑,做好货币政策调控
1、中国转型中的货币政策经验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思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就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因而,在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调控时,货币政策当局和其他宏观调控部门都非常注重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的作用,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计划经济时期现代意义金融部门长期缺失的客观需要,但在政策实践中也确实始终高度重视金融的作用,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分析更加重视金融因素的理论进展相一致,甚至中国的政策实践走在了主流理论的前面。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危机期间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在线修复”、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等政策实践;还有,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采取“不可能三角”角点解的情形进行金融宏观调控,
6
而是根据中国经济金融的实际,探索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的自主独立性的中间解安排,尽管这样的安排加大了预期管理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但在金融稳定、市场发展、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间为政策调控提供了必要的充足空间,总体上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又为加快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并充分把握有利时机,以最终实现清洁浮动的改革目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实践最终都将会丰富主流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理论。
当然,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发展中转轨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货币调控面临的现实条件更加复杂。中国货币政策既要以控制通胀为主还要兼顾转型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体制改革和市场发展的渐进性质,政府管理和调节经济运行仍然多采用信贷限额管理等传统计划经济的工具和手段。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金融环境显著变化,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化,微观主体自主决策的能力和意愿逐步增强,传统行政化、数量型的直接调控效果弱化,需要向市场化、价格型的间接调控转变。二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大量外汇占款导致流动性过剩,应对通胀压力需要高效的对冲操作平台。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共识,而实施资本充足、流动性和杠杆率、衍生产品集中清算等监管要求,都需要金融市场给予足够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依托银行间市场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场深度和广度。实践表明,银行间市场(主要包括货币、债券和外汇市场)在担当调控平台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一是其面向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的特性适合宏观管理部门开展相关调控工作。二是银行间市场的规模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也是中国金融体系中各主要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和投融资管理的主要平台,其承载政策操作和传导政策导向的能力较强。依托银行间市场这一平台,管理部门积极开展常规性和应对危机冲击的各项宏观调控操作。进入新世纪,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市场积极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适时调节市场利率水平和引导市场预期,在缺少足够的国债作为对冲工具条件下,2003年开始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年发行量从2003年的7200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4.2万亿元,有效对冲了流动性过剩,缓解了通胀压力。
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央银行判断准、出手快。较为成功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适时加快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金融业双向开放进一步加深,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面对“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适时调整货币信贷政策,创新并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货币政策总体稳健,与其他宏观政策密切配合,有效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的基本稳定和健康发展。
随着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变化,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流动性环境的变化也导致货币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
7
(PSL)等大量流动性创新管理工具,优化再贷款体系,开展对金融机构的内部评级,在完善金融机构抵押品工具基础上开展信贷资产抵押再贷款工作,不断丰富公开市场操作期限品种,有效弥补了市场流动性数量不足,确保货币市场的平稳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当局肩负着改革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多重使命,在经济结构变迁的不确定环境和理论上存在多重均衡条件下,中国人民银行始终根据经济周期阶段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在有限的政策空间下,通过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积累了大量转轨经济体金融调控和机制建设的宝贵经验。
2、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坚实理论支撑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宏观调控作用日益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宏观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增强针对性和准确性”,这对中央银行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非常重视研究工作对金融改革和货币调控的支撑作用,周小川行长很早就提出了研究立行的重大方针。十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系统紧密围绕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和中央银行的中心工作,通过打造中国金融论坛(CFF)新型智库平台,密切加强与学术界、金融机构和行内业务司局的资源整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央银行“大研究”格局。近年来,中国央行宏观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还以工作论文的形式对外发布,与国内外理论界加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交流,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和货币政策分析的深入开展和健全完善。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人员在我国较早开展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也是构建DSGE模型并针对中国问题开展研究的引领者之一。由于中国面临的经济约束和结构性特征更加复杂,中国央行的研究人员充分意识到,在进行宏观理论研究时不能简单套用国外模型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还应考虑中国特有的体制性因素。例如,研究局开发的DSGE模型根据中国经济金融典型特征进行了大量扩展性工作,引入了影子银行等新型金融部门,增加世代交替特征,引入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部门,并对养老金缺口及其财政影响、财政极限测算、债务置换和房地产政策的宏观影响、潜在产出与经济波动根源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大量扎实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同时,我国中央银行研究人员很早就认识到,虽然DSGE模型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优势,但是其在稳健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DSGE模型主要用于对不同政策效果的模拟,在经济预测等方面并不稳健,特别是短期预测效果很可能并不如VAR和传统计量模型。考虑体制转换因素并引入含体制转换的DSGE模型,或结合传统计量模型构建半结构化的DSGE-VAR模型(Linde et al., 2016),成为DSGE模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事实上,各国中央银行并未完全依赖于DSGE
8
模型进行决策,还大量参考VAR、传统计量经济模型等多种模型的分析结果。例如,美联储就非常重视在结构化方程基础上建立的FRB/US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货币决策中的作用(Fischer,2016c)。我国中央银行的研究人员在结合中国经济金融典型特征对DSGE进行了大量扩展性工作的同时,也建立了新一代的大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并不断探索其他可靠的适合中国实际的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方法。
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过程中,我国中央银行研究人员没有拘泥于现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很多有利于推动金融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如考虑到大量存在着“中间状态”的现实,对经典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进行扩展,探索出中间制度安排理论并应用于中国宏观理论分析(易纲和汤弦,2001);针对国际上流行的金融改革的顺序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统筹协调推进中国的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主张(盛松成和刘西,2015)等等。
三、货币政策的目标框架和操作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凯恩斯主义回归和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推动下,各国货币政策理论和政策操作框架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主要包括:一是价格稳定仍然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但不是经济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危机之前成为主流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受到怀疑;二是以实际利率瞄准自然利率,不应是货币政策操作的全部。从最近几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的经验看,在流动性陷阱条件下,利率政策失效,数量调节更为重要,结构性和差别化的货币信贷政策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三是价格水平的变化是综合现象,不存在与货币供应的简单对应关系;四是货币政策从属于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依据经济金融状况,而不应固守任何机械的政策规则。
(一)货币政策目标框架的新方向
1、有关通胀目标制和货币政策目标的讨论
尽管“大缓和”的原因很多,但以通胀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之一)对经济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新西兰等很多国家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这被认为是宏观经济理论最主要的成就之一(Fischer, 2016b)。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在超低(零、负)利率条件下,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讨论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经济学家们针对提高通胀目标水平、名义GDP目标制、价格水平目标制或结合宏观审慎政策的通胀目标制等可能的选择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Williams, 2016)。
通胀目标制属于复杂的目标规则(Target Rules,Svensson, 2011)。与之相应的泰勒规则是兼顾通胀和产出缺口情况进行利率调整的简单工具规则(Simple Instrument Rules, Taylorand Williams, 2011)。简单泰勒规则在零利率条件下仍然稳健(Gust et al.,2015)。Svensson(2012)也承认,英国、瑞典等通胀目标制国家利率决策主要依赖于当前利率的条件预测,在政策评价上仍存在困难。事实上,近年来货币政策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机抉择倾向(Taylor, 2014)。面对不确定下的
9
经济金融环境,很多通胀目标制国家复杂的目标规则也未得到严格遵守(Kahn and Palmer, 2016)。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政策利率更是长期偏离于Taylor规则所揭示的正常水平(IMF,2008),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重要原因(Nikolsko-Rzhevskyy et al.,2014)。过低的利率促使居民加大消费,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提高杠杆率,并承担更多的风险,从而强化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渠道(Gambacorta, 2009)。因而,在金融市场基本稳定之后,包括Taylor(2015)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强烈主张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当然,伯南克也提出反驳,指出美联储实际操作中会关注很多变量,而不仅仅盯着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
2、坚持以通胀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和货币政策目标框架
与多目标比较而言,货币政策单一目标清晰简洁,易于沟通,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但以通胀水平作为唯一目标的通胀目标制一直都存在争议。相关研究表明,通胀目标制对货币政策绩效的改进主要是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取得的(Sims,2004),而稳定产出的政策效果也是以一定的产出损失为代价(Goncalves and Carvalho,2009)。因此,目前多数中央银行仍然实施多目标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就是典型代表。
中国的社会经济金融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中央银行的多目标制。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处于调整过程中,金融市场也在继续发展过程中,货币政策当局面临的约束条件更为复杂,除了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定目标外,货币当局还肩负着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周小川,2016)。当然,货币政策各个目标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侧重。货币政策的多目标难免重叠并相互干扰,这与复杂货币政策规则一样,容易引发相机抉择倾向。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国际收支外部目标显然应当服从内部目标(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有很大的重叠,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顺利实现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市场稳定等政策目标也是物价稳定的重要前提,而物价稳定也就意味产出缺口为零的经济均衡,也是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自然结果。因此,价格稳定始终是中国最主要的货币政策目标之一。此外,物价稳定更容易量化评估便于操作,以物价稳定为主要优先目标,可以取得类似于货币数量目标制的效果,避免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体现货币政策规则的思想。
在明确将通胀作为货币政策最主要目标之一的同时,还要积极探索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具体形式。与主要发达国家类似,在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的冲击下,中国货币数量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完成,向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趋上升(张晓慧,2015)。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在放弃信贷直接控制后,我国主要采取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模式(周小川,2013)。不过,数量
10
调控和价格调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当数量没有处于合理区间时,价格传导就会出现问题;同样,不考虑价格因素,就会影响数量手段的效率。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在实行间接货币政策调控之初,在充分发挥数量调控作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价格调控的作用,对数量调控存在的“一刀切”、“急刹车”等副作用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放松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通过打造Shibor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等基础性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推动货币政策向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特别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具备了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较为敏感和有效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传导机制。可以说,2015年基本取消存贷款利率管制后,我国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调控已进入以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为核心的深化改革新阶段,这就需要针对利率政策规则进行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加强对中国潜在产出、均衡实际利率等自然率的估算,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利率政策规则。
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行为激励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金融市场结构还不是很完善,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作为传统利率渠道修正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部分微观经济主体对利率的变化还不是很敏感,企业和地方政府也存在投资的冲动,在考量应以货币供应量、信贷量为主还是货币价格为主时应关注二者的波动性及可控性,由此在未来一段时期逐步重视货币价格调控的同时还应关注货币供应量、贷款等流动性的变化。无论从发达经济体在此次金融危机时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经验看,还是从中国货币政策当局过去20年货币政策实践看,中国有效的货币政策不应固守任何机械的政策规则,应依据居民、企业、商业银行行为特征及金融市场状况开展精准调控,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体系的变化而相应调整。
此外,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除通胀目标外,还需要兼顾就业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并且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 Rule,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调节政策和经济调节目标之间关系的法则),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线性无关)。因此,作为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中国央行应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效果,这在近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例如,由于准备金调整可能形成资产负债表效应且信号意义较强,考虑到流动性条件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更多地借助公开市场操作和创新性流动性管理工具,在满足市场不同期限流动性需求的同时,通过适度“精准滴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未来应进一步深入探索、丰富适应中国以通胀为主要政策目标、兼顾其他目标的货币政策理论,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
(二)货币政策操作的新模式
1、中央银行沟通和前瞻性指引
(1)危机以来各国预期管理和前瞻性指引
11
在理性预期革命推动下,各国中央银行都意识到政策沟通和透明度对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性(Blinder et al., 2008)。通过有效引导市场预期,能够使政策操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货币政策也被称作“预期管理的艺术”(Woodford, 2003),预期效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B. Friedman and Kutter, 2011)。全球金融危机后,为稳定金融市场刺激经济,各国都进行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利率降至超低水平并陷入零利率下限困境。为此,各国央行不仅加大了常规沟通的力度,还通过低利率承诺引导公众预期,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成为中央银行沟通和预期管理的重要方式(Carney, 2013)。
尽管大量研究表明,前瞻性指引可以有效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有效性,在零利率条件下很好地引导了公众通胀预期,有助于经济稳定(Ball et al.,2016),但也有很多研究对前瞻性指引效果存在较大分歧(Kool and Thornton, 2015)。作为一项沟通手段的创新性政策,不断修订未来利率路径的前瞻性指引方式并不是稳健可靠的沟通策略,最终可能限制中央银行最优的货币政策路径和政策空间,可能面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损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信誉和政策可靠性(Powell, 2016)。因而,目前美联储主席Yellen(2016a,b)在实践中逐步减少了对前瞻性指引的依赖,更倾向于依靠数据(Data Dependent)进行决策。
(2)健全货币政策沟通机制,提升我国预期管理水平和货币政策有效性
中国人民银行很早就认识到货币政策沟通的重要性,在2009年就明确提出要有效开展通胀预期管理。从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前瞻性指引的实践来看,虽然各方对预期管理和沟通的重要作用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仍有许多开放性的问题值得讨论,包括沟通的程度、沟通的针对性、沟通的技术基础以及最优的沟通策略等。近年来,针对中国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和沟通效果具有一定的效果,但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马勇,2015)。今后应增加信息披露频率、明确性、准确性和一致性,探索多种渠道表达中央银行对经济金融的判断和政策意图并逐步常规化制度化,从而在既定制度框架下提高中央银行货币决策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市场信誉,切实提高货币调控的政策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政策沟通和透明度非常重要,但如果仅依靠预期管理而缺乏其他传统手段的支持,那将只能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货币流动性数量与利率价格显著负相关的流动性效应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利率调控方式的理论基础。Thornton(2004)很早就发现,预期效应和流动性效应是相互促进共同影响利率变化。正如前瞻性指引是为了促进量化宽松的政策效果,非常规的流动性措施也有效促进了利率水平下降并增强了预期管理有效性(Klee et al., 2016)。因此,不能简单地割裂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的关系,预期管理要与流动性管理等传统手段相结合。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在通过持续进行7天回购利率加强短期政策利率引导的同时,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常态化提供流动性,发挥其作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功能。针对不同期限的流动性创新管理工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我国货币市场短期利率、
12
金融市场中长期利率和信贷市场利率传导效率低下的不足。最新的实证检验显示,央行7天回购利率和MLF利率这两个主要的操作利率品种对国债利率和贷款利率的传导效应总体趋于上升,这为畅通转型经济体利率传导渠道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探索。
2、利率走廊机制与中央银行利率引导
(1)存贷款便利与利率走廊机制
由于准备金调整对货币供给影响过于剧烈,而从中央银行获得贷款支持会使得金融机构声誉受损(Stigma Effect),因此法定准备金和再贷款(再贴现)的作用日益弱化(Furfine, 2003),198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三大法宝”仅公开市场操作硕果犹存。与此同时,大额支付系统的采用极大提高了金融市场运行和货币传导效率,因此很多国家都相应改进了货币操作流程(Woodford,2001),实行存贷款便利制度(Deposit and Loan Facilities)和利率走廊机制(Interest Rate Corridor, 或渠道体系,Channel System)。中央银行以贷款便利利率(通常高于目标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以满足其法定准备金或清算账户头寸要求,或以存款便利利率(通常低于目标利率)向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或清算账户存款进行利息补偿,这样市场利率自动锁定在利率走廊区间内,有效稳定了金融机构流动性和利率预期(Whitesell,2006),这一模式逐步被各国广泛采用,全球金融危机后几乎成为各国央行的潮流(Goodhart, 2009)。例如,2003年美联储将贴现窗口改造为自动借款机制,设定贴现利率高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通常高50个基点),成为货币市场利率上限(Furfine, 2003)。2006年美联储获得国会授权于2011年对金融机构准备金付息,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从而在2008年正式形成了双边利率走廊机制。日本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也一度向准备金支付利息,印度、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尝试利率走廊安排。
从各国经验来看,公开市场操作频率提高、双边利率走廊安排和较窄的利率走廊区间,以及对存款准备金进行利息补偿并采取滞后期平均准备金考核方式、加强政策沟通和提高透明度等模式,可以使货币市场利率与中央银行目标水平偏离更小,更有利于中央银行利率引导(Bindseil and Jablecki,2011)。与此同时,利率走廊存在最优适度区间,在市场不健全条件下利率走廊区间可以更大些(欧央行利率走廊区间最初为200个基点,后来降至150个基点)。存款便利利率应低于目标利率,否则机构报价的交易成本溢价将无法得到有效补偿,中央银行将成为市场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澳大利亚将利率走廊区间由20个基点扩大到50个基点的教训就说明了这一点(Woodford, 2001)。不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超低(零)利率条件下,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并将其作为市场利率下限,使得中央银行可以同时控制利率和储备数量,尤其在零利率情形,金融机构愿意保留超额储备,有利于缓解量化宽松的通胀压力(Keister and McAndrews,2009)。
理论上,中央银行贷款和存款的收益和成本应当匹配,因此目标利率通常设定在存贷款利率区间的中间位置,这也被称作政策利率的均衡情形(Woodford, 2001)。不过,金融机构往往要抵押高质量债券才能获得中央银行资金支持,因
13
而均衡存贷利率区间实际上并不是对称的(Whitesell,2006)。全球金融危机后,不对称存贷款利率区间成为讨论的新方向(Goodhart, 2009),很多学者针对中央银行抵押品机制影响(Bindseil and Winkler,2012)及不对称利率走廊区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和宏观审慎政策作用等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Vollmer and Wiese,2016)。还需要注意的是,应在规则指导下决策政策目标利率(Berentsen et al., 2014),否则将无法有效抑制流动性需求。即使是欧元区或英国等采用完备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偏离均衡水平的政策利率同样会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和金融危机。
(2)健全利率走廊机制,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提高中国央行利率引导能力
从政策框架上讲,我国中央银行利率体系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利率走廊”功能(周小川,2013),利率操作模式与国际主流做法差异不大(BIS,2009)。特别是,2015年我国正式取消存贷款比要求并改进准备金考核方式、尝试将SLF利率打造为利率走廊上限,并从2016年2月将每周两次的常规公开市场操作扩展至每日操作,在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都是中央银行利率引导的重要安排,主要通过流动性调节和预期管理,在中央银行利率操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流动性调节主要通过日常的公开市场操作实现,这也是1990年之前各国的主要模式。利率走廊的上下限操作更多地在应对意外冲击和稳定市场预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多数情况下只是“备而不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有机结合,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可以大大提高货币操作效率。
从形成过程来看,利率走廊机制主要与支付系统进步有关,与零准备金制度关系不大,国内有学者对此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所有零准备金要求国家,在引入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时都要求银行在清算账户中保留一定金额的清算头寸,其作用类似于准备金账户考核。各国之所以降低准备金或实行零准备金要求,除了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不宜过多使用外,主要是因为如果准备金不付利息或极低利息,相当于对金融机构征税从而引发其行为扭曲,不利于资源配置和货币政策实施(Feinman,1993),美联储也一直试图说服国会同意其向金融机构准备金付息(Goodfriend, 2002)。2008年之前的50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不大,准备金很少(2007年准备金平均是430亿美元,超额准备金平均是19亿美元)。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能有效影响超额准备金数量,并进而影响联邦基金利率。金融危机开始后,美联储因为救助金融机构以及定量宽松的原因,资产负债表以及其中的准备金急剧增长(2012年前半年准备金平均是1000亿美元,超额准备金平均是1.5万亿美元)。这增加了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联邦基金利率的难度,也就是数量工具的效率下降,迫使美国国会允许美联储对准备金付息。
虽然实行准备金制度会增强金融机构流动性约束,有利于提高中央银行利率引导能力(Bindseil and Jablecki,2011),但准备金的复杂要求和频繁使用将加大流动性外生冲击和市场利率波动。因此,在我国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背景下,要努力探索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走廊机制
14
和准备金管理方式,通过政策操作的协调配合,有效改善市场流动性环境,提高中央银行利率引导能力。
从货币价格调控和利率走廊操作要求上看,中央银行必须明确短端政策目标利率,以此为中心确定利率走廊区间,结合日常的公开市场操作,有效开展市场利率引导。因而,应尽快明确新的短端货币政策利率和目标水平,在改进准备金付息方式和包括SLF在内的再贷款(再贴现)安排的同时,确定适宜宽度的利率走廊区间,形成具有公开、透明、可信的能够真正稳定预期的利率走廊操作框架。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一级交易商制度,在一定标准下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和SLF交易对象范围,完善操作流程,减少市场资金套利机会,降低市场结构因素导致的流动性冲击放大效应,有效开展利率引导。在均衡水平政策利率基础上,探索完善合格抵押品机制,结合MPA等宏观审慎政策,进行贷款便利操作,以确保中央银行资金安全,有效抑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四、经济稳定、金融稳定与广义货币政策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虽然很多国家中央银行也非常重视金融稳定,在发布货币政策报告的同时,也发布金融稳定报告,但由于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并不将金融摩擦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因而出现了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分置的策略倾向。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都将防范金融风险的微观审慎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同时,传统上利率作为唯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就能够有效实现通胀和产出目标,并不需要开展其他的政策操作。但是,全球危机表明,金融部门的作用远超过传统理论的认识,危机巨大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调整是高度非线性的,而零利率下限问题也使得传统利率工具不再有效并面临严重的问题。因而,全球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更加强调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非常规政策手段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这是货币政策调控策略出现的最明显变化。
(一)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及其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1、系统性风险防范与宏观审慎政策
货币经济学传统理论认为,价格和产出稳定能够自动促进金融稳定(Bernanke and Getler, 2001),但金融危机对此形成了巨大挑战,稳定经济环境下金融机构承担了过度风险,金融系统也更加脆弱(Gambacorta,2009)。金融失调对实体经济的负面效应远远超出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预期(Mishkin,2011),金融顺周期性放大了实体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导致经济在恶性循环中不断紧缩。金融危机造成政府债务的急剧攀升(Reinhart and Rogoff, 2009),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使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剧。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现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框架重新审视,中央银行需要关注金融稳定,并寻找审慎政策措施来控制风险(Mishkin, 2010)。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只能控制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但是金融机构间相互作用具有外部性(Acharya, 2009),各机构的风险可以相互传染,较小的风险冲击可能引起严重的系统性事件(Heider et al. 2015)。因此,
15
需要从整体角度进行审慎的管理,也即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来解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和“大而不倒”等问题,IMF、BIS、FSB等国际组织和各国中央银行针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开展了大量研究和政策协调。总的来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分为信贷类、资本类和流动类政策工具(Claessens, 2014),信贷类政策工具主要对金融机构的借款者实施约束(如贷款价值比,LTV,债务收入比,DTI,等等),资本类政策工具关注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包括逆周期的动态资本监管、杠杆率监管、资产负债表约束,等等),流动类政策工具主要关注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主要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准备金、存贷比,等等)。从政策效果来看,大量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维持金融稳定,贷款价值比和负债收入比等信贷类工具可以有效稳定房价和资产价格(Tressel and Zhang, 2016),最低资本金要求等资本类工具能够有效限制杠杆率过度增加(Korinek et al.,2016),流动性指标可以有效扼制流动性风险积累(Cesa-Bianchi and Rebucci, 2016)。
2、加强政策协调,探索完善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我国金融产品体系更加复杂,综合经营趋势明显。同时,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不良金融资产逐步进入风险暴露期,金融市场波动较大,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约束依然严重,经济杠杆风险迅速上升。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与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模式使我国货币调控不仅重视价格指标,更关注流动性和信贷数量和窗口指导的作用,在实践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2003年我国就适时对房地产信贷风险进行防范并通过调节按揭成数和利率杠杆防范房地产泡沫,2004年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分类开展信贷政策,这都体现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并在2015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七个方面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自我约束和自律管理,并在2016年将表外理财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根据资本流动的新特点,在2015年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根据房价和资产价格变化,在2016年继续综合运用贷款价值比(LTV)、债务收入比(DTI)等宏观审慎工具对房地产信贷市场进行逆周期调节的同时,明确提出需要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的作用,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今后,还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统筹做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综合信息统计的管理工作,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丰富符合国情的信贷类、资本类和流动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尤其是针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杠杆率的宏观审慎工具,开展大量基础性研究。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关系也成为国内广泛关注的问题。
16
传统的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货币政策对维护金融稳定存在不足,因此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和互补性,两者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需要密切的协调配合(Shin, 2016)。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市场利率,引起资本充足率的变化,从而影响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通过改变资本金要求等信贷条件,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影响相关利率,并间接改变货币政策立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可以为货币政策产生额外操作空间,影响其传导效率。另外,宏观审慎政策与财政政策、微观审慎政策及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1、“最后贷款人”职责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扩张(量化宽松)和超低(零)利率政策、前瞻性指引及负利率政策等(Borio and Zabai, 2016)。Fischer(2016c)指出,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行使了“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在金融市场面临压力时通过向存款保险机构贷款等方式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有效地减少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低利率政策在降低失业率并稳定通货膨胀率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Fischer, 2016b)。
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危机时期是必要的(Fischer, 2016a),但是在促进危机后经济增长和温和通胀方面,并没有达到人们的期待(Borio and Zabai, 2016),以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由于没有结构性改革的配合,政策效果不及预期,非常规货币政策可能损害中央银行信誉度和政策可靠性(Borio and Zabai, 2016),使得中央银行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损害其独立性(Taylor, 2016)。另外,长时间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容易造成市场流动性过剩,扭曲市场风险偏好,威胁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Gambacorta, 2009)。再有,非常规货币政策加剧了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各国货币政策协调更加困难(Borio and Zabai, 2016)。最后,中央银行还可能面临一定的损失,一旦发生不确定性冲击,货币决策和退出更加困难 (Borio, 2016)。由此,经济学家普遍主张在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开始复苏后应该着手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实现加息和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这也意味着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优化。事实上,美联储早在2010年就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Bernanke, 2010)。近年来,美国经济显著复苏并很可能未来一两年恢复至2%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加息时逐步择机收缩资产负债表成为未来美联储明确的政策方向(Yellen,2016b, 2017)。
2、创新完善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为货币政策和价格调控方式转型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始终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早在上个世纪末就通过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和外汇储备注资的非常规在线修复和紧急救助方式,尽可能快地解决历史存量问题,并通过包括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健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微观金融基础。同时,强调花钱买机制的改革原则,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夯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资本约束,注重做好救助和改革成本的分担与回收,有效避免了道德风险。此后,
17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骤基本都是沿着财务重组、设立股份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发行上市这几个阶段分步实施的,这对于维护金融稳定、改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也极大地增强了货币调控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些政策实践,对于全球金融危机时发达经济体的危机救助方案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存在着如何处理好宏观调控和改革力度的关系问题。过度刺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深层次矛盾,还会导致结构性矛盾的固化,以过度刺激维持所谓的经济高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果是僵尸企业僵而不死、落后产能难以退出。针对近期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用力过猛,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落实和执行力度不到位等问题,提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正是认识到货币政策有其边界,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代替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有效实施需要其他政策配合,尤其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础。
此外,我国正处于数量型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变的关键时期。相较发达国家央行危机以来不断扩表且被动收购资产,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在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局面改变的背景下,调整和优化空间相对较大。如何通过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进一步提高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向价格型货币调控模式转型过程中,要积极探索优化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机制渠道,努力完善创新型政策工具,理顺价格为主的利率工具体系,在资产规模和结构调整的同时,积极优化负债结构并夯实权益资本数量,通过打造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操作灵活、风险可控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为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五、结语
作为与政策紧密相联的学科,现实的挑战始终是货币经济分析理论发展的最大动力。如果真正像“大萧条”和“滞胀”之后那样,经济理论取得飞跃式的进展,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经济金融运行的机制,从而使经济更加平稳健康发展并有效避免金融危机冲击,那么“大衰退”所承受的巨大物质损失也就微不足道了。从经济学二百多年的经历来看,这可以说是“成长的烦恼”。当然,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的步伐并不完全一致,政策实践往往还要慢于应对现实挑战的理论进展。毕竟,按照Keynes(1936)的话说,“政策实践者(Practical Men)通常只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不过,也正因如此,而且“最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这就更要求我们学术界、决策层和市场参与者共同努力,跟踪理论的前沿并将其更好地应用于政策实践,以促进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现实。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政策实践往往超前于理论发现。事实上,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总是在现实的不断冲击下螺旋式上升,而且货币经济分析的所有现代主体几乎总能追寻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或更久远的古老姻亲。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和货币经济理论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作为新兴发展中转轨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仍面临很多挑战。一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
18
有待增强。加强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等领域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是二十多年来各国中央银行共同的经验。改革开放前,银行作为社会资金的出纳长期从属于计划和财政,现代意义的间接货币调控也仅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张晓慧,2015)。因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且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金融功能财政化倾向仍未完全扭转,近期地方债务置换所体现的隐性干预就是直接例证。另一方面,我国宏观调控的制度框架仍待健全,尚未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宏观调控体系。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仍然沿袭上世纪九十年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服务于产业政策和经济增长,缺少逆周期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保障。也正因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才明确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要求。另外,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协调机制的缺失也为货币调控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金融监管缺位、越位、失位现象普遍,尤其是在“封建式”监管格局下,监管与发展职能不分,经常出现“监管行为宏观调控化”的倾向。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完善情况下,金融机构易于扩大规模,增加杠杆,最终倒逼中央银行救助,以致宏观不审慎。此外,中国货币政策一直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在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和促改革缝隙中运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需要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国企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金融监管体系、宏观调控框架、微观主体公司治理等方面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克服各种挑战的同时,有必要及时总结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宝贵经验,将具有全球增长典型范例意义的中国模式提炼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高度。当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边际上的理论创新也是非常艰难的,而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复杂性对决策者更是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对所有研究者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机遇。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当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理论工作者和中央银行研究人员,如何紧盯国际货币经济分析理论的最新进展,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更好地服务货币决策,推动金融改革,通过学术繁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
19
参考文献
[1]. 刘斌,2016,《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第三版,中国金融出版社。
[2]. 马勇,2015,《中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9期,第3~28页。
[3]. 盛松成和刘西,2015,《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中信出版社。
[4]. 易纲和汤弦,2001,《汇率制度的“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基础》,《金融研究》第8期,第5~17页。
[5]. 张晓慧,2015,《货币政策的发展、挑战与前瞻》,《中国金融》第19期,第28~30页。
[6]. 周小川,2013,《新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主要特点》,《中国金融》第2期,第9~14页。
[7]. 周小川,2016,《把握好多目标货币政策:转型的中国经济的视角》,在Michel Camdessus Central Banking Lecture的发言,www.pbc.gov.cn ,6月23日。
[8]. Acharya V., 2009, “A Theory of Systemic Risk and Design of Prudential Bank Regul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5(3): 224-255.
[9]. Ball, L., Gagnon, J., Honohan, P. and Krogstrup, S., 2016, “What Else Can Central Banks Do? Geneva Reports on the World Economy”, 18th Geneva Report.
[10]. Basu, P., M. Gillman and J. Pearlman, 2012, “Inflation, Human Capital and Tobin's Q”,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6(7):1057-1074.
[11]. Berentsen, A., A. Marchesiani and C. Waller, 2014, “Floor Systems for Implementing Monetary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7(3): 523-542.
[12]. Bernanke., B., 2010, “Federal Reserve's Exit Strategy”,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eb., 10th.
[13]. Bernanke, B. and M. Gertler, 1986, “Agency Costs, Collateral,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 Proceeding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14]. Bernanke, B. and M. Gertler, 2001, “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253-257.
[15]. Bindseil, U. and J. Jablecki, 2011, “A Structural Model of Central Bank Operations and Bank Intermediation”, EC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312.
[16]. Bindseil, U. and A. Winkler, 2012, “Dual Liquidity Crises under Alternative Monetary Frameworks”, EC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478.
[17]. BIS, 2009,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s and Central Bank Market Operations”, Market Committee, May.
[18]. Blinder, A., M. Ehrmann, M. Fratzscher, J. Haan and D. Jansen, 2008,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A Survey of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4): 910-945.
[19]. Borio, C., 2016, “Revisting Three Intellectual Pillars of Monetary Policy”, Cato Journal, 36(2): 213-238.
[20]. Borio, C. and A. Zabai, 2016,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 BIS Working Paper, No.570.
[21]. Campbell, J.,2013,”Odyssean Forward Guidance in Monetary Policy: A Primer”,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3(5): 130-138.
[22]. Carney, M, 2013, “Monetary Policy after the Fall”,Speech at Eric J. Hanson Memori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Alberta.
[23]. Cesa-Bianchi, A. and A. Rebucci, 2016, “Does Easing Monetary Policy Increase Financial Instability?”,NBER Working Paper , No.22283.
[24]. Claessens, S., 2014, “An Overview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Tools”, IMF Working Paper, No. WP/14/214.
[25]. Cooley, T. and G. Hansen, 1989, “Inflation Tax in a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4): 733-748.
[26]. DeJong, D. and C. Dave, 2007, Structural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7]. Feinman, J., 1993, “Reserve Requirements: History, Current Practice, and Potential Reform”,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June.
[28]. Friedman, M.,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 1-17.
20
[29]. Friedman, B. and K. Kuttner, 2011, “Implement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in 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3, Friedman, B. and M. Woodford (eds.), 1345-1438. Amsterdam: Elsevier.
[30]. Fischer, S., 2016a,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Fun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Washington, D.C., Feb., 10th.
[31]. Fischer, S., 2016b, “Reflections on Macroeconomics Then and Now”, Speech at 32nd Annual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 Economic Policy Conference, Mar. 7th.
[32]. Fischer, S., 2016c, “Low Interest Rates”, Speech at the 40th Annual Central Banking Semina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Otc. 5th.
[33]. Furfine, C., 2003, “Standing Facilities and Interbank Borrowing: Evidence from the Fed’s New Discount Window”, International Finance, 6(3): 329-347.
[34]. Furman,2014,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View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Report, Feb. 17th.
[35]. Gaballo, G., 2013, “Good Luck or Good Policy?”,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7(12): 2755-2770.
[36]. Gambacorta, L., 2009,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Risk-taking Channel”, BIS Quarterly Review, (December): 43-53.
[37]. Goncalves, C. and A. Carvalho, 2009, “Inflation Targeting Matters: Evidence from OECD Economies' Sacrifice Ratio”,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41(1): 233-243.
[38]. Goodfriend, M., 2002, “Interest on Reserves and Monetary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8(1): 77-84.
[39]. Goodfriend, M. and R. King, 1997, “The 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 and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31-283.
[40]. Goodfriend, M. and B. McCallum, 2007, “Banking and Interest Rates in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4(5): 1480–1507.
[41]. Goodhart, C., 2009, “Liquidity Management”, Paper for the Symposium o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42]. Gust, C, K. Johannsen and D. Lopez-Salido, 2015, “Monetary Policy,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5-099.
[43]. Heider, F., M. Hoerova, and C. Holthausen. 2015. “Liquidity Hoarding and Interbank Market Rat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8(2): 336-354.
[44]. Iacoviello, M. and S. Neri, 2010, “Housing Market Spillover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2): 125-164.
[45]. IMF, 200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46]. Issing, O., 2005, “Why did the Great Inflation not Happen in German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March/April): 329-336.
[47]. Kahn, G., 2009, “Beyond Inflation Targeting”,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Review, 94(3): 35-64.
[48]. Kahn, G. and A. Palmer, 2016, “Monetary Policy at the Zero Lower Boun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Review, (First Quarter): 5-37.
[49]. Keister, T. and J. McAndrews, 2009, “Why are Banks Holding so Many Excess Reserv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15(8): 1-10.
[50]. Keynes, J.,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Macmillan.
[51]. Kiyotaki, N. and J. Moore, 1997, “Credit Cyc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2): 211-248.
[52]. Klee, E., Senyuz, Z. and Yoldas, E., 2016, “Effects of Changing Monetary and Regulatory Policy on Overnight Money Market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6-084.
[53]. Kool, Cl. And D. Thornton, 2015, “How Effective Is Central Bank Forward Guidance?”,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97(4): 303-322.
[54]. Korinek, A. and A. Simsek, 2016, “Liquidity Trap and Excessive Leverage: Datas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3): 699–738.
[55]. Kydland, F., and E. Prescott, 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21
Economy, 85(3): 473-491.
[56]. Kydland, F., and E. Prescott, 1982,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50(6): 1345-1370.
[57]. Linde, J., F. Smets and R. Wouters, 2016,“Challenges for Central Banks´ Macro Models”,SverigesRiksbank Working Papers, No.323.
[58]. Liu, Z., J. Miao and T. Zha, 2016, “Land Prices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80(C): 86-105.
[59]. Lucas, R.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2): 103-124.
[60]. Lucas, R.,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1), P.19-46.
[61]. Mankiw, G., 2006, “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 29-46.
[62]. Mishkin, F., 1997, “The Causes and Propagation of Financial Instability”, in the 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in a Global Econom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Proceedings, 55-96.
[63]. Mishkin, F. 2010. ”Monetary Policy Flexibility,Risk Management,and Financial Disrup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3(3): 242-246.
[64]. Mishkin, F., 2011,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Lessons From The Crisis”, NBER Working Paper, No.16755.
[65]. Nikolsko-Rzhevskyy, A., D. Papell and R. Prodan, 2014, “Deviations from Rules-Based Policy and Their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49(C): 4-17.
[66]. Powell, J., 2016, “Discussion of the Paper ‘Language after Liftoff’ ”, Speech at the 2016 U.S. Monetary Policy Forum, New York, Feb., 26th.
[67]. Reinhart,C.and K.Rogoff, 2009, This Is Different: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8]. Samuelson, P., 1955, Economics.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69]. Shin, H., 2016, “Macroprudential Tools, Their Limits,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Monetary Policy”, in Progress and Confusion: The State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Blanchard, O., R. Rajan, K. Rogoff and L. Summers (eds.). Cambridge: MIT Press.
[70]. Sims,C., 2004, “Limits to Inflation Targeting”, in The Inflation-Targeting Debate, Bernanke, B. and M. Woodford (ed.), 283-308.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71]. Smithin, J., 2003, Controversy on Monet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72]. Stiglitz, J. and A. Weiss,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3): 393-410.
[73]. Svensson, L., 2011, “Inflation Targeting”, in 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3, Friedman, B. and M. Woodford (ed.), 1237-1302. Amsterdam: Elsevier.
[74]. Svensson, L., 2012, “Evaluating Monetary Policy”, in The Taylor Rul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Koening, E., R. Lesson and G. Kahn (ed.), 219-245. Stanford: Hoover Press.
[75]. Taylor, J., 1993, “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39(1): 195-214.
[76]. Taylor, J., 1999,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Monetary Policy Rules”, in Monetary Policy Rules, Taylor, J. (ed.), 319-348.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7]. Taylor, J., 2014, “The Role of Policy in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 Weak Recove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5): 61-66.
[78]. Taylor, J., 2015, “Getting Back to a Rules-Based Monetary Strategy”, Presentation at the 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 Conference, March 20th.
[79]. Taylor, J., 2016, “Can We Restart the Recovery All Over Agai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5):48-51.
[80]. Taylor, J. and J. Williams, 2011, “Simple and Robust Rule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3, Friedman, B. and M. Woodford (ed.), 829-859. Amsterdam: Elsevier.
[81]. Taylor, J. and V. Wieland, 2016, “Finding the Equilibrium Real Interest Rate in a Fog of Policy Devi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No.16109.
22
[82]. Thornton, D, 2004, “The Fed and Short-term Rat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8(3): 475-498.
[83]. Tressel T. and Y. Zhang ,2016, “Effectiveness and Channel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Lessons from the Euro Area”, IMF Working Paper, No.WP/16/04.
[84]. Vollmer, U. and H. Wiese, 2016, “Central Bank Standing Facilities, Counterparty Risk, and OTC-Interbank Lending”,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36(C)L 101–122
[85]. Whitesell, W., 2006, “Interest Rate Corridors and Reserv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3(6): 1177-1195.
[86]. Williams, J., 2016, “Whither Inflation Targeting?”,Presentation to the Hayek Group, Reno, Nevada, Sep. 6th.
[87]. Woodford, M., 2001, “Monetary Policy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Paper for the Symposium o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88]. Woodford, M., 2003, Interest and Pri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9]. Yellen, J., 2016a, “The Outlook, Uncertainty, and Monetary Policy”, Speech at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New York, Mar., 29th.
[90]. Yellen, J., 2016b, “The Federal Reserve's Monetary Policy Toolkit”, Speech at Symposium on Designing Resilient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s for the Future, Aug., 26th.
[91]. Yellen, J., 2016c, “Macroeconomic Research after the Crisis”, Speech at 60th Annual Economic Conference, Oct., 14th.
[92]. Yellen, J. 2017, “The Economic Outlook and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Speeches At 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Jan, 19th.
23
《工作论文》目录
序号
标题
作者
2014年第1号
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
马骏、王红林
2014年第2号
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研究——基于CPI与PPI的相对变化
伍戈、曹红钢
2014年第3号
人民币均衡实际有效汇率与汇率失衡的测度
王彬
2014年第4号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国际改革:路径探微及启示
钟震
2014年第5号
我国包容性金融统计指标体系研究
曾省晖、吴霞、李伟、廖燕平、刘茜
2014年第6号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吴国培、王伟斌、张习宁
2014年第7号
绿色金融政策及在中国的应用
马骏、施娱、姚斌
2014年第8号
离岸市场发展对本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文献综述
伍戈、杨凝
2014年第9号
特征价格法编制我国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的应用研究
王毅、翟春
2014年第10号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马骏、刘斌、贾彦东、洪浩、李建强、姚斌、张翔
2015年第1号
核心通货膨胀测度与应用
王毅、石春华、叶欢
2015年第2号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
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张韶华、王瑱
2015年第3号
移动货币:非洲案例及启示
温信祥、叶晓璐
2015年第4号
我国理财产品收益率曲线构建及实证研究
吴国培、王德惠、付志祥、梁垂芳
2015年第5号
对中国基础通货膨胀指标的研究
Marlene Amstad、叶欢、马国南
2015年第6号
结构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原理及应用研究
朱苏荣、郇志坚
2015年第7号
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
绿色金融工作小组
2015年第8号
关于国际金融基准改革的政策讨论
雷曜
2015年第9号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年中更新)
马骏、刘斌、贾彦东、李建强、洪浩、熊鹭
2015年第10号
城投债发行定价、预算约束与利率市场化
杨娉
2015年第11号
利率传导机制的动态研究
马骏、施康、王红林、王立升
2015年第12号
利率走廊、利率稳定性和调控成本
牛慕鸿、张黎娜、张翔、宋雪涛、马骏
2015年第13号
对当前工业企业产能过剩情况的调查研究——基于江苏省696户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王海慧、孙小光
2015年第14号
“营改增”对中小微企业税负影响的
吴明
24
实证研究——来自浙江省湖州市抽样调查的分析
2015年第15号
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马骏、刘斌、贾彦东、李建强、陈辉、熊鹭
2016年第1号
收益率曲线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马骏、洪浩、贾彦东、张施杭胤、李宏瑾、安国俊
2016年第2号
PPP模式推广困难原因探析及对策建议
崔晓芙、崔凯、徐红芬、李金良、王燕、崔二涛
2016年第3号
企业景气调查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
张萍、潘明霞、计茜、牛立华、范奇
2016年第4号
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体系的传导
纪敏、张翔、牛慕鸿、马骏
2016年第5号
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陈雨露、马勇、阮卓阳
2016年第6号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绿色金融——以浙江湖州为例
洪昊、孙巍
2016年第7号
IMF宏观金融分析内容与方法介绍
尹澄坤、郑桂环、卢心慧、白晶洁、林元吉
2016年第8号
全球避险情绪与资本流动——“二元悖论”成因探析
伍戈、陆简
2016年第9号
2016年宏观经济预测(年中更新)
马骏、刘斌、贾彦东、李建强、陈辉、蒋贤锋、王伟斌
2016年第10号
全局最优视角下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孙国峰、尹航、柴航
2016年第11号
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构建方法:国际经验与启示
吴国培、吕进中、陈宝泉、张燕、吴伟、方晓炜
2016年第12号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度量——基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研究
陶玲、朱迎
2017年第1号
杠杆率结构、水平和金融稳定:理论与经验
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
2017年第2号
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趋向
徐忠
欢迎关注全球金融网微信公众平台
|